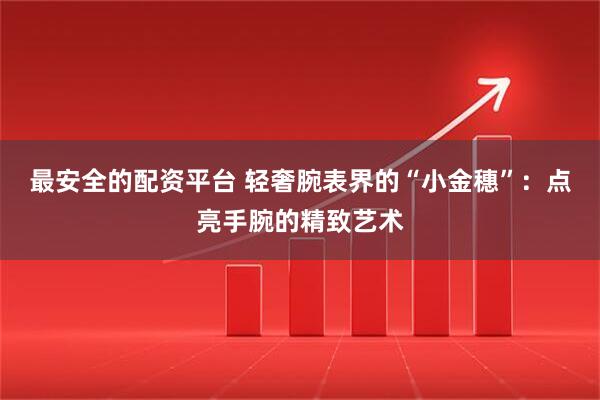1943年的一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西点军校里,一间战术教室格外安静。沙盘上,是蜿蜒起伏的云贵高原和一条叫“赤水”的小河。几名年轻军官推演了几十遍,最终还是无奈摇头。有人叹气道:“如果我是‘上帝’,提前知道红军的路线,也不一定能把他们堵死。”带头感慨的学员,后来成了海湾战争中名噪一时的四星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
让这位绰号“暴风雨诺曼”的美国上将挠头的,不是哪场现代高科技战争,而是1935年初,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指挥的一段经典战役——四渡赤水。在施瓦茨科普夫眼里,这一段机动,几乎是“用上帝视角都打不赢”的战役。
很多人熟悉四渡赤水,是从“以少胜多”这几个字开始的。但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1935年1月的贵州北部,就会发现,故事一开始并不光鲜,甚至可以说是危局四伏。
一、从土城失利,到“掉头再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内召开。这次会议调整了当时中央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决策层,对红军行动的影响,从这时起才真正显现出来。

会议之后,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打算:北上川南,渡过长江,同在川陕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的方针。地图上看,这条路比较直接,目标也清晰:夺取赤水、直逼长江,争取在宜宾、泸州之间强渡。
1月下旬,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先一步占领了土城,准备冲击赤水县城。1月27日,中央准备集中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趁势歼灭川军郭勋祺部,夺取赤水。然而战场上情况很快变得不妙。郭勋祺部顽强抵抗,川军援兵源源不断赶来,红军伤亡上升,攻势受阻。
这种胶着,拖不得。此时距遵义会议结束不过十几天,中央红军的兵力远不足以和川军在当地耗下去。毛泽东敏锐地判断,原定北上渡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硬顶上去,只会陷入对方预设好的“消耗战”。
于是,他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冒险的意见:不要继续死啃赤水,也不要在川南纠缠,干脆果断撤出土城一线,从赤水河边掉头西去,改走川南古蔺方向,寻找新的突破口。简单说,就是“掉头再来”。
1月29日起,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在猿猴场、土城附近架起浮桥,强行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机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一渡赤水”的行动。通过这一渡,红军暂时摆脱了川军正面压力,把主动权从对方手中,硬生生抢回了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西方军校的沙盘推演中,学员们往往会选择“坚守既定方针”,继续沿既定路线向北突击,很难想到毛泽东这样“反其道而行”的拐弯方式。而四渡赤水的高明,恰恰就体现在一个“拐”字上。
红军甩开了川军,却又迎来了新的麻烦。川军领袖刘湘立刻紧张起来,一边加强长江沿线防守,一边指挥部队往川南追击追堵。毛泽东判断,对方的主力被牵到川南是一件“好事”,说明别处的防守就必然变“虚”。

为避免陷入川军包围圈,中央决定再次调整方向,从川南折向云南扎西地区集结。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附近的大河滩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红军现在甩掉大包袱,行动更自由,可以充分发挥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
在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接下来往哪里走?往西去,还是再往东返?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一开始难以接受的判断——回师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在当时的地形和敌情下,这个建议看似“折腾”。好不容易打出川南,结果又要往原路方向拐回去?但毛泽东的盘算很明确:敌人的主力已经被吸到川南一线,黔北相对空虚。利用敌人的调动失误,反向折回,才有机会打开缺口。
二、从重占遵义,到“打不打打鼓新场”
2月中旬,红军按新计划行动,折回黔北。这一下,可算是把蒋介石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各路国民党军主力都盯在长江沿岸和云南扎西一带,黔北只留有王家烈部等地方军队,战斗力有限。
2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桐梓后,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林彪发电报,要求拿下娄山关,趁势夺取遵义城。娄山关是遵义北大门,地形险要,当年孙中山北伐时就吃过这里的苦头。红军打下娄山关,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接着便一鼓作气,攻入遵义。

这次“二占遵义”,对刚经历长征初期连番失利的中央红军来说,是一针强心剂。不止是士气的恢复,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的新指挥路子是行得通的,《红星报》当时的社论就点名称赞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
但战场情势转好,很容易让人乐观乃至大意。正当部队在遵义一带展开活动时,蒋介石在贵阳坐镇调度,准备来个南北夹击,把红军挤死在遵义、鸭溪一线。他采取的是“堡垒主义结合重点进攻”的路数,试图在狭小地区内完成包围合围。
红军内部一些领导人,被二占遵义的胜利冲昏了头,提出趁胜进攻黔军王家烈部所在的打鼓新场,希望再拿一座阵地,扩大战果。毛泽东却强烈反对,认为这个方向不但不“赚”,反而会把红军钉死在一个不利位置上。
据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会上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打打鼓新场,他一度气得提出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后,他找周恩来长谈,详细分析了打鼓新场之战可能带来的后果:一旦在这个方向纠缠,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等部就有机会从四面合围过来,红军机动余地会被迅速压缩。
周恩来听后,态度发生改变。第二天再开会时,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很多年后,毛泽东还提到这段争论,说那时“全场都反对我”,但这个问题上他不能退让。
打不打打鼓新场,在纸面上看,只是一个战术目标的选择,似乎不过是拿下一块地盘的问题。但从整个战略态势看,它其实是“死战”与“机动”的分界线。一旦红军在这里硬上,极有可能被拖成消耗战,重演湘江之痛。

决定不打之后,问题就变成:往哪撤,怎么撤?毛泽东提出,红军要继续保持机动,把战场从敌人重兵云集的圈套里“搬”出去。3月16日,中革军委发布行动命令,红军在茅台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川南区域。这就是“三渡赤水”。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外军的课程讲述里,这里开始出现“看不懂”的感觉:为什么红军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又往西南,看上去像在“兜圈子”?但在毛泽东的安排中,这些似乎杂乱的折返,背后都有清晰目的——调动敌人,打乱对方部署,再从缝隙中找到突破口。
三、虚虚实实的三渡、四渡:让对手摸不着头脑
红军三渡赤水之后,蒋介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红军多半是顶不住了,要赌一把再次北上渡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样一来,只要把长江防线守死,再在川南地区布下重兵,就有机会在古蔺、叙永一带“聚歼”中央红军。
蒋介石于是下令中央军、滇军、川军往川南集中,亲自下电令强调“此乃聚歼匪之良机”。从他的角度看,红军在他设想的包围圈附近来回折腾,就是“网中之鱼”。
但毛泽东的打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决定走一招极险的棋:再一次渡回赤水河,从敌军云集的区域旁边绕过去,以佯攻和突然折向的方式,引导敌人“走错路”。

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一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做出了一副“要攻贵阳、再东进湖南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从表面看,红军似乎准备向东突击,直逼贵州省城。
蒋介石果然上了当。他判断红军必然从贵阳以东,沿马场坪、镇远方向东下,威胁湘西,于是急忙把滇军、中央军调往贵阳周围,加强贵州中部防线,准备在北盘江中游一带截击。
但毛泽东真正的用意,在于再一次“拐弯”。敌军主力往贵阳周围集中,贵阳以西、以南的兵力自然出现空档。红军趁对手调动之际,从北盘江下游突然西渡,绕过重兵防线,一路向黔西南运动,继而进入云南,甩开了数十万国民党军。
这一连串动作,三渡赤水偏向“虚”,主要目的是调动敌人;四渡赤水偏向“实”,则真正为南渡乌江、再上金沙江创造了条件。
如果将这一段战役打包来看:从1935年1月底土城战斗失利开始,到4月初红军转至云南,前后不过五十多天,中央红军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穿插,变换方向七次。一路打了数十场战斗,最重要的却不是歼敌数量,而是一次次挣脱包围,把生命线从敌人手里抢了出来。
很多年后,刘伯承在回顾中说,遵义会议后,红军“好像忽然获得新生命”,以穿插、迂回把敌人耍得团团转——“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这句话,用在四渡赤水上,尤其贴切。
四、孙子兵法的“水势”,在赤水河边活了过来

西方军校会把四渡赤水当作必讲案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段战役把《孙子兵法》里一些抽象的东西,变成了活生生的战场实践。
《孙子兵法》说:“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意思并不复杂:水要顺着地形流,军队则要适应敌情变化。如果硬往上冲,迟早会被“地形”绊倒。而毛泽东在赤水河两岸的指挥,正是用“水”的思路来用兵。
一渡,是避锋芒;二渡,是抓空虚;三渡,有意“作势”,让敌人以为红军穷于奔命;四渡,则是在虚实转换中,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每一步看似只是“转移路线”,实则都是在利用敌情变化,调整自己的“水道”。
值得一提的是,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完整方案。并不存在一个“提前写好的剧本”,从一渡到四渡照着念。每一次转向,都是在敌我态势发生新变化后,根据当时情况作出的决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不断实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原则。
毛泽东在扎西会上的讲话,点得很明白:红军的作战路线,要服从于大的作战方向。一条路被堵死了,就要敢于换方向;敌人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抓住不放,转到对己方更有利的地区去。他强调要利用敌人的过失,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主动寻找战机,而不是被动站在原地挨打。
在很多古代军事家的理解里,“虚”与“实”更多是静态的:这里守军少是虚,那里重兵屯集是实,打仗就是从“实”处寻找“虚点”下手。但四渡赤水体现出的虚实观念,更进一步——“虚”可以是故意做出来的,“实”可以是转瞬即逝的。红军通过自身行动,主动制造和改变“虚实”,不只是“利用地形”,而是主动“重塑态势”。

红军三渡赤水,表面上是往敌人的重兵方向移动,实际上是在诱导敌军调动。而四渡,真正关键的是渡北盘江、再渡乌江,最后走上金沙江北岸,完成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前提步骤。从这个角度看,“四渡赤水”的“终点”,并不在赤水河,而是远在金沙江畔。
在整个过程中,中央红军在战略上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能集中优势就集中,集中不了就拉开距离,等新的机会。表面上看像是在“躲”,实则是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这种“能伸能缩”的掌握度,不得不说异常罕见。
五、虚实相即:让敌人帮着完成自己的布局
聂荣臻后来回忆,二渡赤水前,红军内部有不少干部对“回头走老路”的决定不理解,觉得费了这么大劲折到川南,又折回黔北,像在“打圈子”。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专门给全体指战员写了一封信,说明为什么要不断转移作战地区。
信里讲得很直接:红军必须寻找有利条件去消灭敌人,不利条件下就要拒绝那些没把握的战斗。为此,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赢得胜利。这种看法,与《孙子兵法》中“虚实相生”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
传统对“虚实”的理解,大多停留在静态层面:哪里防守严密就是“实”,哪里兵力空虚就是“虚”。而在四渡赤水中,“虚”与“实”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动态过程。红军用自己的运动,故意在敌人视线中塑造一个“虚实错位”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要攻贵阳,实则是为西渡北盘江争取时间;表面上绕着川南打转,其实是在把敌人往预定的方向牵扯。

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在贵州、云南一线的大规模调兵,本身就成了红军的一部分“兵势”——他越紧张,越集中力量堵红军设想中的“出路”,那些真正的出路反而越显得空荡。
彭德怀当年领导红三军团,亲身经历了这段机动。他后来评价说,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从贵阳西北绕到城东,再从南面迂回到西边,摆脱了四面包围,最后胜利渡过金沙江,他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的”。这种敬佩,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场硬仗,而是针对整盘棋局的布局能力。
再往大一点看,如果说湘江战役时的中央红军,是在被动挨打、被动突围,那么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已经掌握住了主动。敌人布防一次,红军变一次;敌人调兵一次,红军又换一次方向。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让“兵无常势”的古老教训,从书上的字,变成了山间辙印。
1935年春夏,中央红军最终甩开了在贵州、云南境内追堵的数十万国民党军,转至四川西部地区,继而在同年6月初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进发,为后来的会师创造了条件。如果把湘江到金沙江这一段路程作为一个整体看,四渡赤水无疑是转折之点。没有这一段在云贵高原的曲折穿插,就谈不上后来的北上与会合。
从地图上看,四渡赤水不过是在一条河,两省交界间来回绕了几个弯;从战争史角度看,这些弯却极大改变了长征进程中的力量对比,把一支被数十万大军围堵的队伍,硬生生从死地引到了生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世界军事学院会把这段战役列入重点案例反复剖析。
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兵书的人来说,赤水河畔的那几次渡河,不只是机动作战的胜利,也是对“兵者,诡道也”“兵无常势,无恒形”的一次极为生动的注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古人称之为“神”;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这种“神”,真实地出现过。
扬帆证劵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